“飞越疯人院”:中国留学生自述加拿大精神病院住院经历(组图)
我是一名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学的留学生。两年前,我曾经短暂地在精神病院住过院。今年疫情发生后,我原本要参加的一个后续的心理课程,一下子没了下文。这两年,我的病情从最开始发作到现在逐渐恢复的过程,虽然充满了艰难,但所幸调整得不错,所以疫情的冲击对我的影响并不大。但这让我想起来,现在有同样困难的人的处境,会比我艰难得多,于是决定记录下这一段经历,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状况,也算是对自己这两年的经历做一个交代。
2018年11月底我在和同学吃饭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后全身颤抖,心跳加速,手脚发麻以至于无法独立行走,随后在同学的搀扶下坐上了Uber并前往多伦多总医院(Toronto General)的急诊科就医。在经过两小时的漫长等待后,医生终于出现,他判断睡眠不良是诱因,因此开了安眠药便草草了事。
于第一次发病之后,又陆续有几个晚上我感到精神极度紧张,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我分别前往Hamilton General Hospital和St Joseph Hospital的急诊室就诊,均因生理指标正常而被医生告知不做诊断并且不提供用药建议。在陆续前往医院急诊但并未得到有效诊断治疗之后,我的情况没有好转,甚至每况愈下。2018年12月23日那一周,是我有记忆以来最难熬的一周。
在经历了四天每晚彻夜未眠(心率过高,手脚发麻以及精神紧张导致)和食欲不振之后,在第五天,只吃下了几片饺子皮(肉馅恶心,吃不下),然后又是一晚的彻夜未眠:起床,静坐,躺下,如此反复。这种前所未有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让我感到生命是如此的煎熬。我在一天唯一的活动煮饺子的时候看着发红发热的炉灶竟产生了想用手去摸,并通过灼伤的疼痛来转移我的注意力的想法。在次日凌晨,我搭乘uber,再次来到St Joseph Hospital。了解到St Joseph主治精神类疾病,我在挂号处恳求护士让我看心理医生而不是普通的急诊医生(普通急诊医生肯定又会让我回家呆着,再这样在家呆下去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次遇到的挂号的护士人比较好,同意了我的要求。一如既往在急诊大厅等待两三个小时之后,一个St Joseph精神部门急诊的护士来向我询问了一些事宜并把我带进了一个独立的区域。这个独立的区域只有一个门进出,里面又分为两个区,一个是普通的休息诊断区,另一个则是特别观察区。我在普通休息诊断区坐着等待护士问询,医生诊断,整整从上午十点坐到晚上十点,期间医生给我服用了1mg Lorazepam并建议我进食一些简单餐品。
在休息诊断区坐这么久主要是因为我恳求医生让我住院,因为我当时十分恐惧自己回家,害怕自己死在家里都没人能帮。多名医生和护士在反复问询我之后同意了我的住院请求,并在当晚带我坐电梯上到医院最顶层的精神疾病住院区。上面提到的特别观察区,设计感觉类似牢房,因为墙和地面是水泥的,不过每个小间并没有门,类似隔断。
我是因为上卫生间而进入到这个特别观察区了一次,出入的时候都要护士开门禁才能打开进出此区域的铁门。在等待的期间,由于我的房门是敞开的,曾看到一个手被绑住的二十岁左右的女性被两个高大的男性拖进特别观察区,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病人的家属,一名三四十岁的女人,跟在他们后面。医院顶层的精神疾病住院区也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我和大部分病人住的普通病房,房间十分宽敞,两人一间,进出房间的门很大并且不能关闭,应该和一般住院病房一样是方便推手术车进出;另一部分则类似于急诊那里的特别观察区,每个病人独立一间,每个房间都是大铁门锁上,门上有一个加固的小窗口,护士的办公室则直面这些特别观察区的病房,整个区域和其他普通病房区域隔离开来。
在住院的第一天早上,我和我的室友正式认识(头天晚上太晚都已经睡了)。他不是市里人,开车来Hamilton见她的女朋友(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本来觉得交流得挺好可能要准备组建新家庭了,他却在进医院的前一天突然发病了。他的病名字叫bipolar disorder,中文是狂躁忧郁症。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很暴躁有时候又很抑郁,而他发病的时候正好是他突然暴躁的时候。他说他当时也不太能控制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把一切都搞砸了,本来就要步入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却因为bipolar disorder毁了一切。
我们在这里的病人大家多是同病相怜,互相鼓励,不过他情绪正常的时候看起来都有点吓人,可能是因为是村里人,乡土气比较浓一点,就给人一种比较野的感觉,所以我也是有点怕他。不过他又给我展示了他在中国城买的Bruce Lee的T恤,说他很喜欢李小龙,我们又交流了一些中国武术的东西,也算是熟识了。
起床不久他就讲了一句很经典因此我至今记忆尤新的话“Nothing makes me feel more like a human than a good shower in the morning“。或许洗澡这种最原始最本能的放松调节活动对于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病人来说也算是生活里不多的快乐来源了吧。洗澡过后他带我去就餐区取餐,每个人的餐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和服药情况有关。
吃饭的地方同时也是公共休闲区,有电视,乒乓球台子,杂志和桌游等。手机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但是充电器在入院时候就被统一收走,在住院区充电需要去专门的地方。(收充电器是因为充电器算尖锐金属,属于危险物品)在第一天的下午,我迎来了我住院以后的第一次会诊,到场的有医生、护士、社工还有实习医生等等,总之阵式很大,有点多对一面试的感觉,很让人紧张,尽管医生肯定会尽量通过话术、情绪渲染等方式让会诊有一个轻松的氛围。会诊的内容大概就是重新再问一大堆已经问过无数遍的问题:来这里之前的情况,现在的感受,有没有自残和伤害他人的想法等等。一想到在充电台边上的宣传海报上赫然写着“We won’t need you to tell the same story again“,也是十分的讽刺,实际上每次不同医生会诊都会把差不多的问题再问一次,我总共被问了四五遍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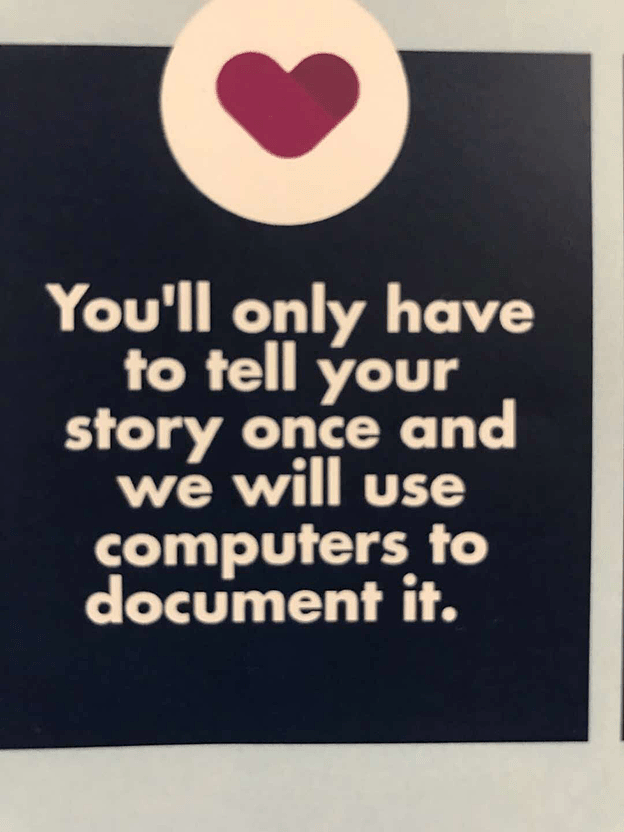
在公共休息区,我又有幸认识了其他的一些病人:有和男朋友在加拿大辛苦打拼工作却现在因为bipolar住院同时遭遇感情危机的华人女生;有逢人就讲他八岁就有了自己的手枪还吓唬别人自己杀过人的老爷子killer John;有刚从特别观察区被准许转入普通住院区就不放过一个机会下楼抽支烟的原来公司的女强人奶奶;还有看起来对刚说的这位奶奶含情脉脉的另一个痴情老爷子。除了聊天,我还会和华人女生打打乒乓球(因为别人可能也不会),和室友还有另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玩桌游,和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看电视、画填色绘本,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




在经过两天会诊之后,医生们觉得我可以和大学校医院建立联系并在家长期服药调整,同时给其他的病人腾床位了。所以在短暂的三天住院结束后,我和病友们一一道别,大家欢送着我离开了这个神奇的地方。通过这次精神病院之旅,我才了解自己是患上了Anxiety disorder 焦虑症;发病原因很多:特定激素分泌水平低,睡眠质量差,外界紧张环境刺激都可能诱发panic attack(惊恐症);目前我长期服用sertraline调节,随身携带lorazepam备用。
其实我到临走时候才了解到我其实一直是voluntarily hospitalized,而我的病友们基本都是involuntarily hospitalized。这两种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可以随时要求离开医院,但他们必须经过医生同意之后才可以出院并且每天只能下楼30分钟而且不能离开医院的这个区域。所以当我在搭乘着uber回家的途中,望着湛蓝的天空,突然意识到自由真的是很宝贵的。
原来的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情绪、行为很多时候自己也不太能控制,并且大多因此生活陷入困境并且进入限制了自由的医院治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有些人甚至还可以把自己的经历滔滔不绝地编成故事讲给你听。于我来说,我很感激住院的经历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让我认识了解到了社会上的这一群人。希望每个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有机会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毕竟一生太短,禁不起浪费。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